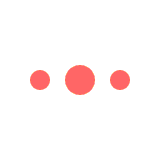情满人间PPT
故事分享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走进作者林奕含的往事与文字下沉甸甸的心情房思琪和刘怡婷是一对“灵魂的双胞胎”。她们喜欢同样的作家,连背书都会一起忘记同...
故事分享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走进作者林奕含的往事与文字下沉甸甸的心情房思琪和刘怡婷是一对“灵魂的双胞胎”。她们喜欢同样的作家,连背书都会一起忘记同一个段落,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要好。而在她们13岁的豆蔻年华,却因为脸蛋的不同,开始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思琪非常漂亮,怡婷其貌不扬。楼下的国文老师李国华,也正是看上了思琪的漂亮,计谋诱奸,便假借给二人补习为由,让她们每周到家里交一篇作文,制造和思琪单独相处的机会。之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李国华控制、并且不断性侵房思琪,用“文学”的养分滋养思琪的灵魂,又让她的灵魂欺骗她的身体。思琪试图对身边的人诉说,对妈妈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和老师在一起。”妈妈回答:“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对好朋友怡婷说:“我和老师在一起了。”怡婷回答:“你真恶心。”唯一一次差点对伊纹姐姐说出口了,到嘴边也只能憋出一句:“我觉得李老师怪怪的。”一直到最后实在无法承受心灵的痛苦,思琪疯了。也是那之后,怡婷才从好友的日记里获得事实的真相,为自己曾经的无知而痛苦不堪。作者林奕含在生前接受了一家媒体的专访,她说:“这个故事其实用非常残酷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这是一个女孩子爱上诱奸犯的故事。”但她却用了很细,乃至于过细的文字去书写人、内心、文字。为什么她要这样做?实际上,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故事,新闻,会有同情,会感到不舒服,会感到难过,但这到底算什么呢?我们真的能够理解经历如此沉重的痛苦的女孩子,她们内心的感受吗?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就在即将开始新的人生,梦想才刚刚发芽的阶段,却因为粗暴凶残的打击而断送一切的滋味吗?恐怕不容易。作者林奕含希望通过细致的文字,让我们这些还算有点良知的旁观者能够触碰这种伤痛的边缘,哪怕一点点也好,那么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就可能有一个“房思琪”,因为这样的触碰能够活下去。看似柔弱胆怯的林奕含在书中用一种含蓄却执着甚至是顽强的方式做出了抗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学形式的抗争“文学”作为一种表达形式,被赋予了思想、情感,乃至艺术的美感,被人们向往着,崇拜着。人们可能很少思考过“文学”本身可能会有正义与邪恶、黑色与白色的两面性,可能会因为“不正确”的使用而被灌注“帮凶”的标签,作为一种“工具”,被“不正确”的思想所滥用。在作者林奕含自杀前八天的专访中,她透露小说里的“李国华”不仅在生活中有原型,也有其精神原型——胡兰成。张爱玲与胡兰成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把自己在三个女人之间的恶行用文学诡辩为“不可以解说”的“人世之理”,将自己强暴小周、背叛张爱玲的行为解释为“仁义”,就像李国华把对房思琪的侵犯解读为“爱”,把色情暴虐的场景形容为“曹衣带水、吴带当风”。这种畸形的思想体系被文学美化,开脱了犯罪者的残酷,洗白了施虐者的无耻。作者在小说中不断叩问,这难道就是她从小热爱的“文学”的真正用途吗?难道是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孕育出了这样畸形的思想体系?而这样的思想体系的病原体,恐怕来自封建大一统王朝的极端权力对女性身体无条件征用。李国华在小说里喜欢搜集“黄袍”带回家,她的妻子看不明白,这实际上是李国华骨子里的“皇帝梦”在作祟,通过对女性身体的侵犯、欺辱,以达到自己对权力与控制的满足。林奕含在文学形式上采用了非常新颖的手法对文学的“诡辩”进行质问,她称之为“误用”。比如她写道:“温暖的是体液,良莠的是体力,恭喜的是初血,俭省的是保险套,让步的是人生。”这里的形容在感情上都是不对称的,在那样的情况下的感受绝不应该是“温暖”的,而作者却“误用”了词汇,以此来叩问“文学”的“立场”,颠覆词语应有的舒适,带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思考。精神的抗争作者本人是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的,她在精神科医生和药物的帮助下不断尝试改变,但是非常困难。她表示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陷入情绪中无法自拔,痛苦到极点,而她还是想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提出:“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就是将内心压抑的欲望表现出来,白日梦同样也是愿望的达成。”弗洛伊德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很难不把“房思琪”和“林奕含”联想在一起。作者在这样一种虚构性较强的而又并非完全虚构的创作中,是想要将内心压抑的愤怒表达出来的。在第二章《失乐园》中,作者写道:“房思琪的书架就是她想要跳下洛丽塔之岛却被海给吐回沙滩的记录簿。洛丽塔之岛,他问津问渡未果的神秘之岛。”尝试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可进行对话。